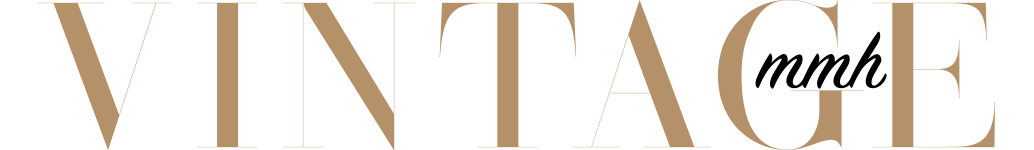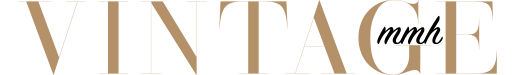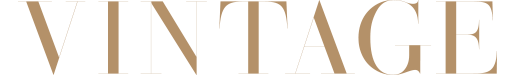「我總是習慣在平面繪畫與立體裝置作品之間反覆來去,以求能找尋更貼近自我的創作語言。」── 莊普
資料提供@Text by 張禮豪、Photo from莊普
今天,當我們回顧廿世紀充滿眾多變化的文化發展時,自1960年代興起的「極簡主義」(Minimalism)以反對藝術形式的傳統區分定義,主張透過簡單而直觀的藝術感知,將重點更多放在美學、結構與材料上,既挑戰了藝術既定的創作、欣賞與感受方式,也突顯觀眾、作品與空間環境之間的體驗與互動,直到現在仍是極具革命性與開創性的重要見解。
極簡主義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除了視覺藝術之外,包括具有強調量體的視覺衝擊、材料的豐富表現、巧妙而精緻的構造等特色的建築與傢俱設計,乃至於充滿實驗性的音樂、文學等類別都在其中,也徹底改變人們對於一切事物的思考方式,像是眾所皆知的「包浩斯(Bauhaus)」整合不同藝術領域的思考核心更是被廣泛應用在各個領域當中,留下了非凡的影響力。



從生活中挖掘更多的美學趣味
而我們若是回到極簡主義藝術在台灣的歷史發展脈絡來看,那麼甫於2019年獲得第21屆國家文藝獎殊榮的莊普(1947-)擅長從日常中挖掘更多的美學趣味,透過不同創作媒材的交織演繹,來反映一己對於生活、社會乃至於自然環境的觀察與感知,無疑是繼林壽宇(1933-2011)之後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藝術家。
按照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其著作《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中所論,進入機械複製時代之後的藝術作品已然打破了既定的時空限制,無法如同傳統藝術一般,可以藉由特定時空情境的在場來構成其獨一無二的「本真性」(authentic),尤其置身於真實與虛擬的界線日益模糊、一切熟悉的判準都可被翻轉、甚至徹底改寫的當代,更是讓人憂心是否就此再無一絲一毫「靈光」(aura)倖存的可能?幸好,刻正於台中國立美術館展出的「越野的靈光:莊普個展」,無疑給出了一個足堪欣慰的答案。


此次展覽,則是其近幾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足以令觀者得以一窺其自1980年代迄今四十多年未曾中斷的藝術發展歷程與變化。事實上,貫穿莊普整個創作發展歷程的核心,即是立基在極簡主義的美學觀念與實踐之上。如策展人石瑞仁所言,透過這個展覽,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平面繪畫創作不斷演繹其獨有的印記手法,開展出超越極簡主義美學概念的旨趣;另一方面則巧妙運用日常生活所見的事物與訊息,轉化為擴大觀者想像的承載工具。
像是在展中創作時間較早的《來去自如遨遊四方》一作中,莊普將既像是現成物,又像刻意打造的不銹鋼管,藉由彎折出斜線直角橫伸的作法,完成了十分類似將人們慣見的迴紋針放大成立體作品,難分究竟何處起始、何處而為終結之樣貌,讓「物質」產生獨立的存在意識,同時也呈現出極簡藝術與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兼具的美學趣味。復刻1992年的《逃離現場》一作將大量上漆的木材廢料或彎或折或平放在牆上與地面,在經意和不經意間讓看似平淡無其的材質搖身一變為猶如散發出某種「靈光」氣息的所在(Site),無疑也提醒著你我從慣習出走的必要。


依地創作的《召喚神話》則結合充滿懷舊意象的各色木製門窗,打造出由廿多座幾何抽象三角柱體所組成的龐大類建築量體,觀眾在穿梭其中時或可輕易聯想起散落在台灣各地眷村的住宅聚落,以及過去時空熟悉的生活風情;《光塵尺度》裝置作品則以建築設計必備的魯班尺自天花板筆直垂掛而下,直至地面上彷彿承接飛泉流瀑的水盤為止,既延續了自杜象(Marcel Duchamp,1887-1968)以降的現成物創作美學,亦能得見些許東方傳統美學想像,令人玩味再三。


此外,其繪畫以一公分見方的印章來取代畫筆,儼然最具個人風格的代表性手法。透過反覆的身體勞動,讓看來不甚均整的印記在畫面上既可重重疊加,也能無限延伸,成功地開展出一條跨越文化與媒材的藝術路徑。無論是從英國浪漫主義畫家泰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銳意捕捉光線在空氣中一瞬即逝的變化效果汲取靈感,或是借鑿南宋馬(遠)夏(圭)以概括簡練的構圖來描繪一邊半角之景,莊普近年體察到自身創作時尤其關注光的折射與分析等物理現象,包括《夜暖嫩綠草叢間》等幾件晚近的平面作品除了援用慣見的印記手法,還加上充滿書寫質地的線條結構,使其精心佈局的極簡藝術形式下,更多是蘊藏其中的感性詩意,都不難見到其遊走在東、西方藝術文化歷史脈絡中的自在與自信。
對莊普而言,創作乃是一種歷經理性邏輯與學術理論爬梳之後的「頓悟」,正如禪學對於語言文字的破解,讓一己的內在思想得到全然的解放。踏入其以印記筆線,乃至於各種物件所建構而成的極簡心靈空間,我們彷彿也能跟著他跨越了形式與內容的對應框架,進而感受到心靈與材質交會時閃耀的一抹靈光。